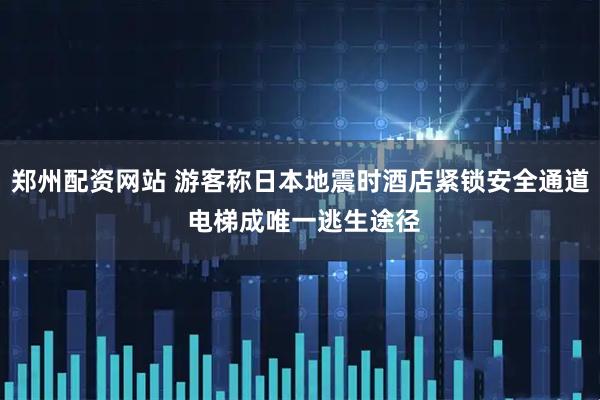“我一见他君臣来赔礼……”秋日清晨,53岁的史其生一边哼着豫剧《杨八姐游春》郑州配资网站,一边在家楼下停稳外卖车。车筐里的保温袋已经送空,他却还沉浸在戏曲的韵律中,手指不自觉地打着拍子。路过的邻里对此早已司空见惯,一位闲坐的大爷笑熟络地向他喊话,点名要听下一段《穆桂英挂帅》。
记者 阮西内 摄
从河南到浙江平湖,二十三年时光流转,史其生早已在这座浙北小城扎根。他披上蓝衣的皮肤,是穿行城市的骑手;褪去工装,换上戏服的皮肤,便是沉醉韵味的票友。两重皮肤,一重托起现实,一重举起理想。
初心
脱下蓝色的外卖工装,他推开里间的房门。十余平方米的空间里,一块幕布简易搭着唱戏的舞台。衣柜里,从金线绣龙的蟒袍到威武挺拔的生衣,五十余套戏服整齐排列。衣架上,则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式戏曲盔帽,从帝王的平天冠到武将的夫子盔,一应俱全。三面墙上,腰带、头饰等配饰排列得整整齐齐。这满堂华彩,与记者进门时所见的简朴装饰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展开剩余84%史其生在家里献唱。记者 阮西内 摄
这份热爱,记忆中始于儿时。“7岁那年,父母牵着我去赶会。”史其生的记忆里,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项城,每年的赶会是全村最热闹的时候。
土台子一搭,红幔布一挂,锣鼓一响。他看着台上的《包青天》,“‘包青天’一开口,唱腔又刚又正,台下老百姓都拍手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叫‘正气’,就是觉得心里特别敞亮,特别快乐。”
这种最朴素的快乐,像种子一样埋进了他心里。
受访者供图
高中时,他开始攒钱买豫剧磁带。“每个月零花钱二十多块,我攒了半年才买得起一盒《包青天》。”虽然买完才发现没钱买录像机,但他并不后悔,“光是听着唱腔,就觉得很满足”。
1991年元旦晚会,他第一次登台演唱《包青天》。“台下掌声响起来的时候,我手都在抖。”那种被认可的喜悦,让他心里的戏芽真正扎了根。
如今,他的抽屉里还珍藏着五六十盒磁带。“每次整理这些磁带,就像翻看老照片,每一盒都记录着一段时光。”
2002年冬天,为了改善家境,他来到平湖打工。制衣厂的工作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,“累得站着都能睡着,但不管多累,哼两句戏就舒坦了。”
后来成为外卖员,等餐的间隙、送完单的空档,都成了他的练声时间。“有时候骑着车,脑子里闪过一段戏词,就轻轻哼着。风一吹,好像连赶路的累都飘散了。”
说着,他从衣柜里小心捧出一套龙袍戏服,虽然陈旧,但干净挺括,看得出经常打理。“这是我的第一套戏服,陪我走过十多年了,当时花了大半个月工资买的。”他说道。
求索
“我扮上给你们唱一段。”他利落地换上戏服,坐在镜前打开那个用了多年的油彩盒。凡士林打底、勾勒眉形、涂抹底彩……镜中,外卖小哥渐渐隐去,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眉目含威的戏曲老生。
“最早学化妆,是对着手机照片一点点试的。”史其生翻出手机里的旧照片,画面里的他画着老生脸谱,眉峰画得有些歪,“那时候下班回家就对着镜子练,画完了自己看不顺眼,就擦掉重来,直到满意为止”。
随后,他站起身,水袖一甩,“宋王爷传下来一道圣旨……”唱的是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。声音浑厚有力,手势精准到位,眼随手走,每一个眼神都透着戏。
受访者供图
“以前可没这么规范。”史其生翻出手机里2012年前的录像,那时的他全靠自己摸索,对着电视学,手势是乱的,唱腔是飘的,“有时候觉得自己唱得不错,录下来一听,完全不是那个味儿。”
转变出现在2012年当时任职的企业举办的晚会上。“部门经理听说我会唱豫剧,特意安排我登台。那是我第一次在平湖唱家乡戏。”出乎意料的是,他刚唱完第一段,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演出结束后,还有同事专门来找他学唱豫剧。
这次经历让他坚定走专业路线,不能再停留在“自娱自乐”的阶段了。
寻找同好的路从此开始。他加入一个个豫剧群,发现这里聚集着200多名票友,多是在天南海北的河南老乡。大家把录音视频发到群里,互相点评唱腔、切磋身段。在这个虚拟的“戏台”上,草根爱好者们抱团成长。
2015年,史其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通过QQ群联系到一级演员袁国营,独自前往郑州拜师。
“在见袁老师的路上,我把戏词背了一遍又一遍。”回忆起那个下午,他眼里依然闪着光。袁老师听他唱完《三哭殿》,一针见血:“唱得太急,要像走路一样,一步一步踩实。”
2021年冬天,史其生被嘉兴市戏曲家协会秘书长马其林看中,在他的引荐下,史其生多了一个新身份——嘉兴市戏曲家协会会员。“在业余爱好者中,他的唱腔和舞台表现力都很突出,更重要的是那份对戏曲的敬畏心。”马其林说。
绽放
随着表演日趋专业,史其生推开了一扇更大的门。
养老院里,他唱起《花木兰》,赢得满堂欢笑;社区文化礼堂中,他的《穆桂英挂帅》引得观众跟着打拍子;最令他自豪的,是与四百余人同台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,“一个字都不能唱错”。
十年戏梦,被他珍藏于相册。小生、老生、花脸……不同角色见证着他在舞台上的一次次“绽放”。谈及豫剧与越剧之别,他认真解释:“豫剧唱腔通用性强,行当界限相对模糊,讲究‘一人千面’——演员通过调整音色、音量和润腔方法,就能塑造不同年龄、身份的角色。而越剧行当划分更精细,唱腔区分明显。”
至今,史其生已完成超过50场演出。每次登台,他都精心准备:戏服必熨平,妆容必细描。“要对得起舞台,对得起观众。”最让他感动的是有观众等在台口合影,夸他“唱得真有味儿”。“我一个普通人,能在异乡因家乡戏被认可。这种快乐,什么都比不了。”
有人问,唱戏会影响跑单吗?史其生笑着摇摇头。外卖工作偶有委屈,但豫剧恰是他的情绪出口。“有时候送餐受了气,可只要哼上两句戏,那股闷气就随风飘散了。”他坦言,这份爱好成为了他穿梭城市巷陌时最好的陪伴。等餐时默念戏词,骑行路上练气息,已成为他的习惯。“一段戏哼完,几单外卖也送到了,心情也畅快了。”
这份执着也赢得了家人的支持。妻子朱凤芝从最初觉得“买戏服不如改善生活”,转变为他的忠实观众,不仅帮他整理行头,还会录制演出、陪他回看改进。
部分荣誉证书。
“接下来要继续磨唱腔,”史其生规划清晰,“每天坚持‘啊——’音爬坡练声,把声音‘打远’。”学习的路径也愈发开阔,“网上有视频课,群里能交流,身边还有老师。只要想进步,处处是课堂”。采访结束,他瞥了眼手机:“午高峰到了,得去跑单了。”
蓝色电瓶车汇入车流。城市里,多了一个带着戏韵奔跑的骑手,也多了一个在烟火气中坚守热爱的普通人。
“转载请注明出处”郑州配资网站
发布于:北京市广盛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